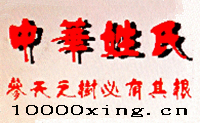《散文天下》绿天长寂苏雪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- 中华苏氏网 2011年9月15日 网络
.jpg)
苏雪林(1897年2月24日 —1999年4月21日,享年102岁)原名苏梅,字雪林,笔名绿漪。一生跨越两个世纪,杏坛执教50载,创作生涯70年,出版著作40部。她一生从事教育,先后在沪江大学、安徽大学、武汉大学任教。后到台湾师范大学、成功大学任教。她笔耕不辍,被喻为文坛的常青树。她的作品涵盖小说、散文、戏剧、文艺批评,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成绩卓著。
对于她而言,无论远观还是近察,都像西洋的印象画,色彩绚丽,斑驳陆离,难以准确地界定画中的景致。她像一个禁区、一个隐语,一首朦胧诗,一个让人永远无法猜透的谜。
她是一个才女,是中国文学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。“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”,“台湾文学的祖母”,“三十年代五大女作家之一”,更被《孽海花》作者曾朴赞为“闺中大苏”。这些光环使她历经风雨显得更加夺人眼目。
她又是一个侠客,有着惊世骇俗的举动。反鲁、包办婚姻、皈依天主教,她在五四的新文化中接受洗礼,却又忠诚于传统的旧道德,她在那个战火纷飞、狼烟四起的年代,孤身展开了激烈的笔战,即便丢盔弃甲也义无反顾。
她是一个太过矛盾的结合体,让人看不懂、识不清、参不透。这,注定了她深深的寂寞。她是苏雪林。
一
岭下苏村位于黄山脚下、太平湖北岸。村庄三面环山,南面水口,形似天然圈椅,聚气生财。河水蜿蜒穿村而过。村口有一亩丹桂参天蔽日,十里飘香。而今走进村内,依然粉墙矗矗,鸳瓦鳞鳞,是一个极典型的徽派村落。
清末之际,徽商的身影依然活跃在江浙的商界。苏运卿,这个从岭下苏村走出去的眉山苏辙后裔,在营商过程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,此时,已经商而优则仕,执掌着浙江省瑞安县衙的大印。
十九世纪末,伴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,西学东渐,资本主义思潮开始涌进了古老的华夏文明。苏运卿的儿子苏锡爵已经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,儿媳亦出身于仕宦之家。
1897年,阳春三月,一个女婴的啼哭声从瑞安县衙里传出,声音倔强有力,这个女婴就是苏雪林。她的祖父正是苏运卿。
苏雪林当时的小名叫瑞奴、小妹,学名小梅。这都是徽州坊间对女孩的普遍称谓。尽管出身在书香官宦世家,可谁也没把她当作小姐。祖母更是斥之为野丫头。
年幼的小梅有着男孩子一般的脾性。她和叔叔、哥哥们一道抡刀舞棒、扳弓射箭,一道捉蟋蟀、放风筝、钓鱼、捕鸟,玩得十分开心。然而,及至读书年龄,叔叔、哥哥们都纷纷去私塾读书了,小梅却只能在家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。没有了玩伴,孤单寂寞被无限地放大了开来,小梅能做的,不过是终日地怅望大院那四角的天空。
顽强的小草只要有点滴的水份都可以活下去。幸亏,命运给小梅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。她的叔叔、哥哥们求学带回家的书籍、报刊,成了丰富的精神食粮,滋养着小梅幼小的心田。十三岁时,她灵感突发写下了七绝《种花》:“满地残红绿满枝,宵来风雨太凄其。荷锄且种海棠去,蝴蝶随人过小池。”
压抑得越久,或许才会有更多的叛逆和反抗吧。在那个被高墙遮挡住了阳光的阴晦的童年,小梅讨厌憎恨祖母,和父亲关系淡漠,惟一的温暖来自任劳任怨、和顺持家的母亲。母爱,成了她久旱中的甘霖,沙漠中的绿洲。
十五岁时,小梅随母亲迁回了老家岭下苏村。距村南二里地的石墈上,曾有五座石牌坊列于道旁,牌坊上分别嵌有“流芳千古”、“表正伦常”、“冰清玉洁”、“德协坤贞”、“光争日月”的石匾。牌坊下草色青青,虫声唧唧,仰望那黑矗矗如徽墨般的牌坊和石匾,尚梳着羊角小辫的小梅能读懂它们吗?
命运似乎格外眷顾这位天资聪颖的女孩。不久,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,小梅得知消息后,“费了无数眼泪、哭泣、哀求、吵闹”,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。她后来回忆说:……愈遭压抑,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。当燃烧到白热点时,竟弄得不茶不饭,如醉如痴,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,名为“水上”的树林里徘徊来去,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,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,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,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,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。
鸿鹄一旦脱离了牢笼必将一飞冲天。此间,正值五四新文化思潮澎湃兴起,小梅仿佛一条涸辙的鱼儿游进了大海,在省立初级女子师范毕业后,她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继续深造,并以高才和卓识显露出出众的文学才华,“安徽才女苏梅”迅速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。一九二一年,小梅在即将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时,又考取了海外中法大学绘画系,等待她去领略的,将是法兰西的激情与浪漫。
邮轮犁开了道道浪花,她的人生似乎展现出大海般无边的广阔。
二
爱情是什么?是李清照和赵明诚的两情相悦,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生死相契,是一束火红的玫瑰,但有时又是一杯香艳的毒酒。
爱情,也是一场美丽的疾病。在法兰西这个浪漫的国度,小梅病倒了。
二十出头,正是花季少女的豆蔻年华。哪个少女不怀春,又何谈深受新思潮影响之苏梅!曾见过小梅年轻时的照片,面目端庄,气质不凡,颇具大家闺秀之风范,想来身边应不乏追求者。史海浩瀚,我们已无从考证,只知道法国留学期间,她曾真心爱上一个青年,这个青年也非常爱她。在誉为“法国粉红色的心脏”的里昂城,古老的街头巷尾应处处留下了他们罗曼蒂克的身影吧。谁曾想到,历经漫漫长夜内心痛苦地挣扎后,小梅竟亲手扼杀了这甜蜜而狂热的初恋!她说:这是我平生第一个光荣的胜仗,值得我自己歌颂称道无穷的。
只因父母早已在家给她包办了婚姻。
斯人已去,我们不知道小梅在说那句话时心中是怎样的滋味,不知道小梅对将来那个托付终身的人又有着怎样的期许和等待?
张宝龄,原籍江西南昌,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,后赴美留学,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。在这个工程师的脑中,或许都是密密麻麻的公式、定律和数字吧!他又如何与小梅雅歌投壶,诗酒唱和?如何光风霁月,文采风流?
一纸婚约,胜同班师回朝的十二道令牌。在连续三次拒绝家里的催婚后,小梅万般无奈,不得不匆匆辍学,于1925年提前回国,和订婚十几年尚未谋面的未婚夫完婚。在岭下苏村,至今仍保存着小梅新婚居住的房屋“荆乐堂”,婚房内很简单的几件家具,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显得略有破败,小梅就在这个小房间把自己交付给了一个她毫无爱意的男人。
此前两年,与她同窗又是同事的好友庐隐,在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姻后,不顾家庭、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,与有妇之夫郭梦良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。一片谴责声中,倒是小梅坚定地站了出来为她辩护,说批评者,不应当拿平凡的尺,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。
对友人的选择给予了积极的支持,却把自己牢牢拴在了旧传统上,谁也无法真正说清小梅的想法。也许是幼受庭训不愿伤害病榻上的母亲?也许是欣赏未婚夫的品学?也许是不愿背负朝三暮四、反复无常的恶名?
婚后的生活自然是枯寂无趣的。此后两人辗转上海、苏州、武汉等地,聚少离多,而且并未生育有子女。晚年回忆此事,小梅发出良多感慨:譬如他有事赴北京月余,竟半个字也不给我。更道是:结婚虽三十六年,同居不到四年。关系之冷淡可见一斑。然而她又坚持不离婚,因为“总觉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,总是不雅”。
没有爱的婚姻,是深深的寂寞。内心越寂寞,越渴望爱的来临,这恐怕是个悖论吧。新婚后,小梅把这一份寂寞化作了散文集《绿天》。在那涂满绿色的天空下,有绿荫蔽日的园子,温柔的溪水,山芋地,蝶儿蜂儿鱼儿花儿,还有一对执手玩耍的新人。这分明就是一曲幸福的田园乐章。温情旖旎的爱情生活场景,足以让任何一对恩爱的夫妻羡煞!
然而,这不过是个“美丽的谎言”。
翌年,小梅又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《棘心》。她在“前题”中写道:我以我的血和泪,刻骨的疚心,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,纪念我最爱的母亲。书中的主人公杜醒秋是一位“五四”时代的女性,她内心充满了痛苦、矛盾、失望和悲愤。她相信科学,却又皈依宗教;她追求爱情的甜蜜,却又遵从父母之命。小梅当时的心境从中可窥一二。
两本书都是以“绿漪”为笔名发表。
应了这段失败的婚姻,过去那个怀着少女梦的小梅已经消失了,我们看见的是一位新文学的代表绿漪女士。晚年她在回顾这段感情时,用了两个字:感谢。细细品之,有着难以名状的苍凉。
三
在绿漪的生命中,有两位重要的男人:鲁迅和胡适。
绿漪半生反鲁,世人皆知。最惊世骇俗之举,当是在1936年11月鲁迅逝世后,写下《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》,拉开了她“反鲁”的序幕。过四天,她又写下《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》,继续对鲁迅进行抨击。
三十年代的旧中国,正是左翼文学大行其道的时期。鲁迅作为左翼文学的领袖,以杂文为匕首、投枪,揭露国民的劣根性,投身革命战争和救亡道路,深受无数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拥戴,逝后更是被誉为“民族魂”,身份和地位不容亵渎。绿漪的这种行为,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结果自然是可知的。蔡元培仍然参加了鲁迅的治丧委员会,胡适肯定了“鲁迅自有他的长处”。绿漪顿时陷入了四面楚歌、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然而绿漪偏有一股头撞南墙的意思。直至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《我论鲁迅》,才宣告半生的“反鲁”事业结束,“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”。
付出的代价是,绿漪已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“化外之人”。
其实,绿漪早间和鲁迅并无积怨,她对鲁迅的感情,甚至是钦敬。《绿天》一出版,她很快就送给了鲁迅,还在扉页上题写了:“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、四、一九二八”字样。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对鲁迅的态度忽然发生三百六十度的转变?是政治因素、性格因素还是情感因素?后人揣度不免有些臆测,或许这已成一段文学公案了罢。
惟一无可否认的是,斗转星移,曾经沧海,但鲁迅已经深深烙进了绿漪的生命里。尽管他们一生只有过一次会面,那是在1928年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上。半个多世纪后,绿漪以九十四岁高龄在自传中还写了一笔:鲁迅对我神情傲慢,我也仅对他点了一下头。短短一句,绿漪的感受与心态,却是情见乎词,跃然纸上。
对胡适这位徽州老乡,绿漪却有着另一种复杂的感情,可以称之为爱慕吧。早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听胡适授课时,她就对这位留美博士的翩翩儒士风采产生了深刻的印象。胡适亦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颇有好感。此后多年,两人鱼雁往来,教学相长,循循善诱,或探讨文学和思想,或交流红学和屈赋研究心得,成就一段美谈。在多次笔墨官司中,胡适也是挺身而出,保护和支持了绿漪。
回忆与胡适的种种交往细节,绿漪的心理感受显得十分细腻和微妙。她在自传中写到:在胡适招呼她共享茶点的时候,她竟然羞怯地走掉了;在胡适家的客厅里对坐的时候,她竟然觉得有种受宠若惊、亦幻亦真的恍惚;她是一个感情比较麻木的人,但在胡适逝世后,她竟然悲痛至极,连自己都不能理解那种奇异的经验……
同乡谊,师生情,柏拉图式恋,已然难以分清。
这种深厚的情谊一致延续达四十余年,直至胡适撒手人寰。之后,绿漪在胡适逝世一周年发表纪念文章《伤麟——适之先生周年祭》,逝世五周年出版纪念文集《眼泪的海》。1982年,胡适逝世二十周年,年已七十有五的绿漪,又出版《犹大之吻》。煌煌两本纪念文集,计有二十四万余字。
追慕之情由此可鉴。
敢爱敢恨,直爽真诚,这正是绿漪之可爱处。在对待这两个男人的态度上,绿漪身上的文人之真性情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或许,这才是绿漪,即便陷入无边的寂寥中,依然义无反顾、勇往直前,哪怕头破血流,哪怕粉身碎骨……
四
性格决定命运,这话用在绿漪的身上一点不假。笔墨的官司,最终还是她输了,输得彻彻底底。这也是她在1949年抛别所挚爱的大姐与优渥高尚的大学教职工作,毅然远走他乡,辗转香港、法国,最后寄身台湾的直接原因吧。
僻居孤岛,绿漪的灵魂已经全部交给了屈赋,交给了故人和故纸。
一别就是半个多世纪。
胡马依北风,越鸟朝南枝。在那湾浅浅的海峡之后,在成功大学的校园里,萧瑟的秋风中,凋零的木叶下,绿漪或许不止一次地向北方遥望吧。万里明月,星汉无声,那杏花春雨的江南,或许曾不止一次出现在梦中,萦绕在心头?
浓浓故园情、深深家国恋,满腔的相思化作绿漪笔下的篇篇美文,她写父亲、母亲、姐姐,写山村的过年轶事,写儿时的种种印象。她也画画,1993年,台湾出版了《苏雪林山水》,收入七十五幅美术精品,竟然都是描述岭下苏村和黄山的风景。她还养猫,但终究排遣不了心中的寂寞。年事欲高而思乡欲切,她终于决定要回家了!
五月,正是黄山最美的时节。杜鹃红艳,群莺满树,天空似洗过的一片湛蓝。1998年5月27日,一百零二岁高龄的绿漪横渡海峡奔波万里回到了故乡。此时,距绿漪离乡已达七十三年之遥。黄山依然是那样的奇险峻秀,而昔年的青丝红颜如今已是白发如霜的老者!
在乡人的鞭炮声中,绿漪踏上了久别的故土,凝视着渴望已久的岭下山水,她谒宗祠,访旧居,坐闺房,听松泉,面对这遥远而又熟悉的景物浮想联翩,流连忘返,老泪纵横,她不停地说:我不走,我不走,这是我的家。也许是被老人的真情所感动,幼时发蒙读书的海宁学舍内干枯多年的紫薇花竟为之绽放。斯人、斯景,令人唏嘘。
回家,是所有漂泊游子的夙愿。我们且把绿漪的这次回乡称做还愿之旅吧。谁也不会知道,这位古稀老人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从家乡返回台南后,绿漪把姐姐坟旁的墓地送给已经年高古稀的外甥,对他说:将来,你在台南陪你的妈妈,我要去陪我的妈妈了。
一年后,绿漪在台南辞世,终年一百零三岁。她的骨灰被送回安徽岭下苏村。“我深信我的母亲常在我身边,直到我最后的一日。”绿漪1939年深情地写进她散文里的这句话,竟一语成谶。这位“五四的最后一位作家”又回到了儿时玩耍读书的小山村,静静地陪伴在母亲的身边。
绿漪墓前,乡人特意将“流芳千古”这块古牌坊上留下的青石匾额,端置于墓的上方,褐色大理石墓碑的背面镌刻着八个大字:
棘心不死 绿天永存
在她长眠的凤形山下,养育她的岭下苏村一览无余,晨雾蔼蔼,夕烟袅袅,穿村而过的松川河水,一如《绿天》中的那样活泼和快乐……
后记:
面对苏雪林,我们很难轻易臧否,下一个简单的结论。在胡适去世时,苏雪林写过一副挽联,其中一句是“提倡新文化,实践旧道德,一代完人光史册”。其前两句“提倡新文化,实践旧道德”或可用来概括她矛盾、复杂而寂寞的一生。
当年胡适函复苏雪林谈及对鲁迅的评价时说:他已死了,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,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,究竟经过几度变迁,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,否定的是些什么,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,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。
古人云:不废江河万古流。当今研究评价苏雪林,或许同样应该如此罢。

分享按钮>>千十二派---灵山坞十烈士
>>中华燕氏宗亲联谊会湖南分会沉痛悼念燕丕攸宗亲逝世